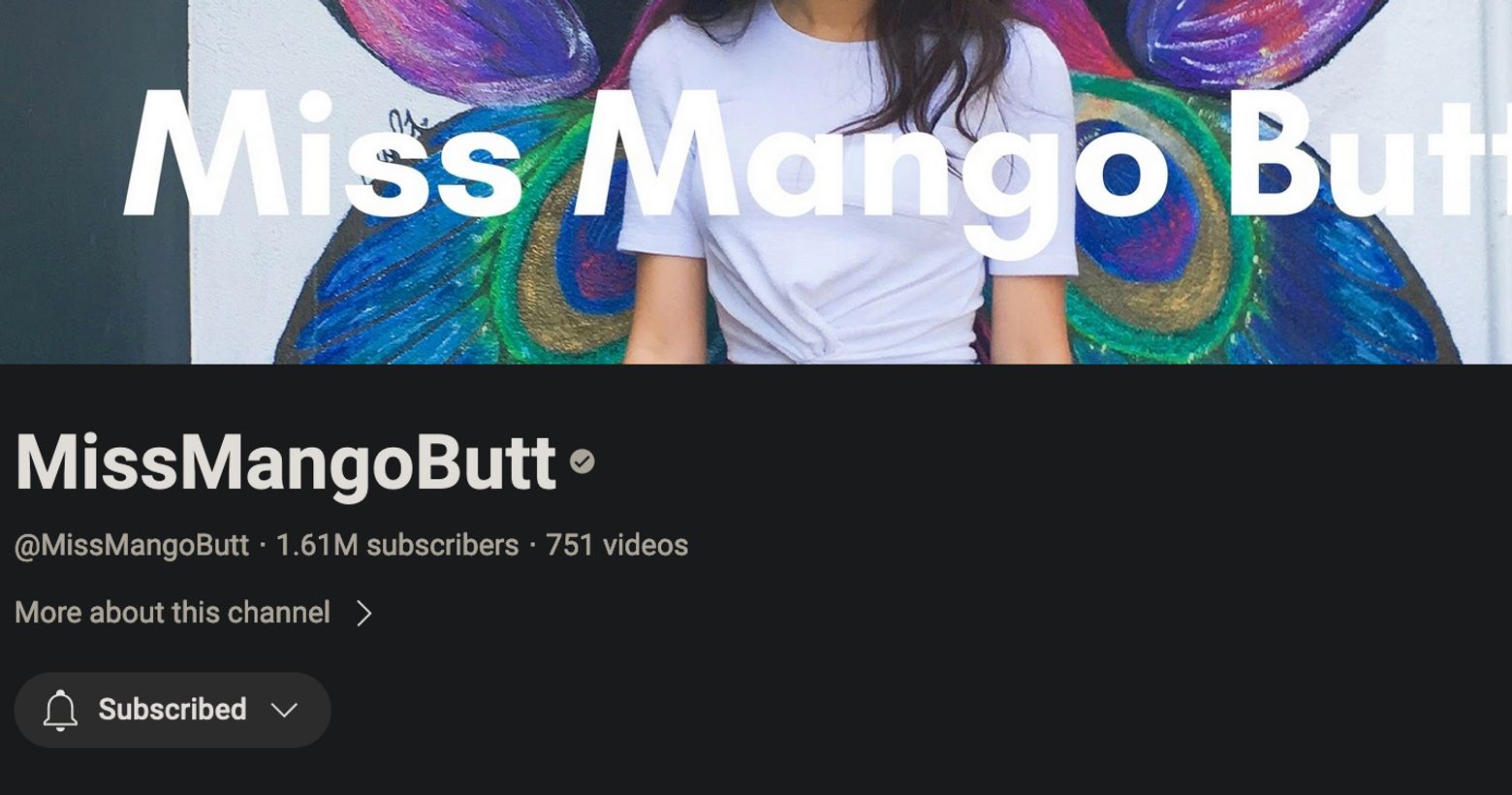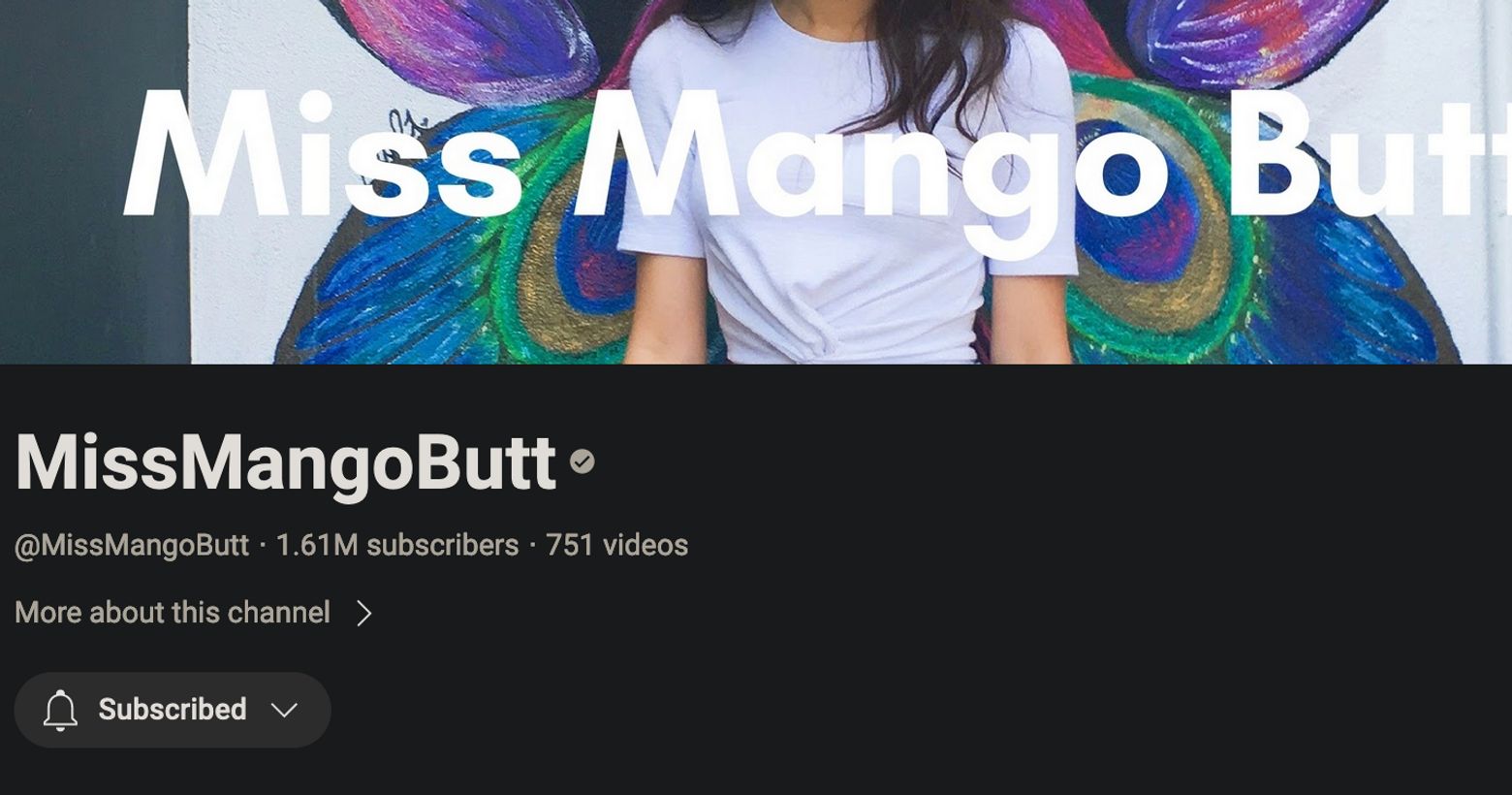關於十二月的陽光
2021/12/07-12/10
近期的所有事物彷彿都像十二月的陽光,轉瞬即逝。甚至在前進的過程,都輕易預見了可能發生的消失。像是朝一年的終點走去,開始懷疑後面還有沒有接續的路面,或者只存在一個斷崖。沒有以後。沒有更多。
可這一路上卻從不寧靜。窸窣聲響不曾間斷。有時音量稍微大一些,便有了清晰的詞語輪廓。那樣不好,資訊的重量和隨附的共感成為綑綁在身上的鉛塊,下沉只是必然而不可抗的結果。
他們彼此間話語的銳利與爭鋒相對,情緒的起伏與表情的變化,全都讓關係變得危脆。他們的,以及我與自己的。儘管至始至終都只是個旁觀者。可因為本就排斥,甚至恐懼這樣高頻波動的行為,一切像毛細現象般擴展出去,來不及逃,便被淹沒了。而堅實的表象彷彿忽然都只是單薄的冰層,以為恆常永固,實則脆弱地不堪一擊。這些情景從身外不停向核心侵蝕,讓持有信念不再那麼容易。因此時常停下來質問。起初依然能夠篤定,爾後卻越來越常迷失在問題的回音裡。代表心臟的腔室是中空的。沒有答案,沒有信仰。
而我是何其畏懼這樣的自己。害怕所以退縮,但退縮以後將一無所有。那可是關乎生命意義的信念啊。竟然也同等脆弱。甚至脆弱得不堪入眼。
特別是當一切都發生在十二月。相對陰暗濕冷的十二月。悶滯,生活在碗底的十二月。沒有對流,沒有前進。
我習慣蜷縮在主體的窗口下,緊貼著牆,仰賴冬日裡微弱的自然光,翻揀藏收起的破敗。有時蹲在那裡,把它們一一攤開,看看有沒有哪些部分還能湊合。卻似乎從來沒成功過。依稀記得某年的十二月,我在囊袋裡什麼都沒摸出來。連個碎塊也沒有。那是一個淪陷在無感迴圈裡的冬天。究竟是無感的一無所獲好,還是持有揭示自身脆弱的破敗好。這個問題像無限也無止境的回聲,已經存在了好久。曾經有過答案,卻又再度遲疑。更發覺有時候在後者的狀況裡,竟自然地演示起了無感。
這大概是因為去看見那些單薄又脆弱的面向,去正視,一直都過分裸露。像冷冽的風從傷口的細縫裡吹進皮層。我一直以為這種疼痛在重複之中是能夠被習慣的,後來發現那些佯裝成的無感,底下都是活生生的感受。「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數不清到底有過多少次,但每次的傷害對我來說都是那麼深刻的重擊。每一次那種痛的感覺都是那麼用力、那麼真實的打在我身上。」她平靜的說。對強烈的感受始終無法習慣,卻對自己每一次仍然會出現的疼痛習以為常。面對自己的脆弱也一樣。只是這多了厭惡的情緒。那種因為無法滿足自身期許強大而失望的情緒。只是因為無論如何嘗試,我仍然是一片薄冰,容易化去,卻也容易破碎。這樣的徒勞是那麼地傷心。
或許,這些確實都像十二月的陽光,轉瞬即逝。但在每一次被照耀和觸碰的時候,仍然會由心的感到幸福和安全。或許真的沒有恆常,或許從來沒有永固,或許本身的信念就是過分理想,或許一切就真的只是隨時會消失的冬陽,甚至海市蜃樓,連真實性的判別都變得困難。但所有的溫度卻都是最大化的。更值得最用力的擁抱。儘管被擁抱的時候,知道終究會迎來分離。然而,我說的、我所相信的篤定,從來不是實質上的「你與我永遠共存」,是精神和心靈上的,擁有過作為一種永恆。
「如果有一天,我說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退開了,你一定要來追我好嗎?因為我只是退開了,卻從來沒有真正離開。你來了,我一定會跟著你回到我們的原點。」過度的言說。濫情的書寫。我依然相信這是在偌大飄盪裡找到屬於關係和我們的篤定的,唯一途徑。就算一切終究只能像十二月的陽光,也仍然致力在被照耀的當下,留住最多的溫度,成就意涵上的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