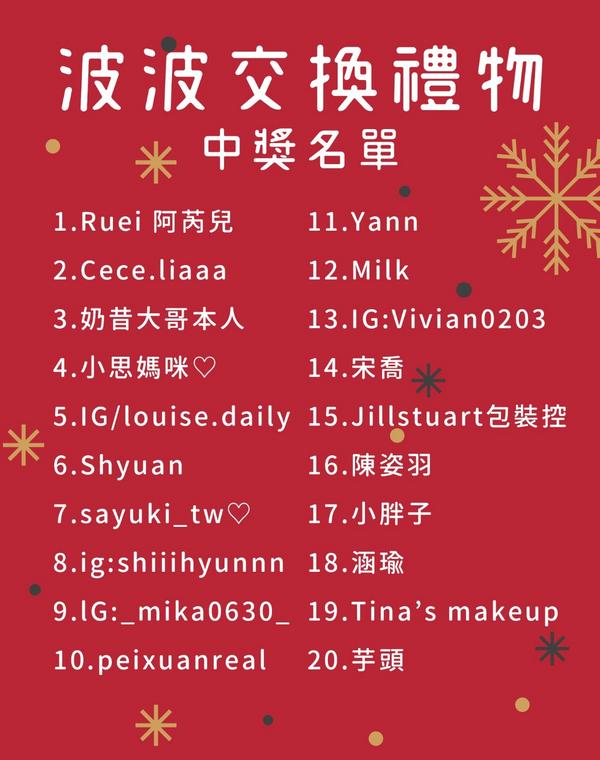【恐怖】永‧安…永遠安息
哐!關上了大門,我打開了客廳的燈。
走進了很久沒有整理的房間,隨意丟下了行李,便直直撲向那張想念已久的床。
倒下、深呼吸。
床單和枕套上熟悉的味道,替內心帶來一股平靜和溫暖。
家,我終於回來了!
明天是除夕,家家戶戶都準備要返鄉過節。
當我從營區趕搭夜車回來,踏進家門也已是凌晨兩點的事了。
一路上舟車勞頓,讓我一見到床就只想賴在床上,動也不想動。
突然,我想起了一件讓人非常不爽的事!
話說…在我當兵的這些日子以來,說好聽點是磨練,說難聽則是受苦受難。
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回家過年,家人卻偏偏選在這個時間點出國旅遊,讓我既羨慕又心寒!
他們倒好,開開心心的跑去北海道玩,獨留我一個人,正好替他們看門。
靠,搞什麼,當兵要留守,回家也要留守,啥鬼!
早知道就不回來了,還不如找幾個兄弟們一起去玩個兩、三天也好。
只是…在這樣的節日裡,每個人都想回家吃團圓飯,哪還有人陪我去玩啊?
算了,越想越氣,難得可以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想這麼多還不如睡覺算了。
肚子突然咕嚕了幾聲,我那正準備休眠的腦袋突然就想起了-「雞排」。
張開了眼睛,一股莫名的興奮翻騰,我起身拎著鑰匙和皮夾便往巷口走去。
凌晨兩點半,應該有個賣鹽酥雞的攤位還在營業。
「阿伯,一份雞排加辣。」來的有點晚,架上的食物都已經快被掃光了。
「肖年耶,你放假哦?(台)」賣鹽酥雞的阿伯一見到我,便很熱情的招呼著。
「對啊,剛回來。」我報以開心的笑容,回應著阿伯給我的溫暖。
「體型越來越勇哦,你來的嘟嘟好,雞排只剩最後一塊,我快收攤了,這個四季豆和杏鮑菇就送你吃啦。」阿伯很阿沙力的把架上剩下的蔬菜全都丟到炸鍋裡炸了起來。
「阿伯,這樣歹勢啦,你會了錢啦!(台)」阿伯向來都對我很好,只是這種看似貪小便宜的行為讓我很不好意思。
「三八啦,煩惱加多衝啥。(台)」阿伯手腳俐落的在炸鍋裡攪動著滋滋作響的炸物。
「就要收攤了,身體也有點不舒服,想早點回去休息啦。」阿伯笑笑的說著,看起來不像是有什麼病狀的樣子。
「阿伯,你看起來好好的啊,是哪裡不舒服啊?」
阿伯六十歲了,除了星期一是他的公休日之外,其他的日子都會到巷口擺攤賣鹽酥雞。
雖然上了年紀身體本來就很容易故障,但阿伯平時身體很好,聽他這麼說,倒讓我有些意外。
「嘸啥啦,這炸好了,快拿去吃。(台)」阿伯將炸物灑上了辣粉,再裝進袋裡包好了遞給我。
我一手接過袋子,另一手拎著要付的錢,只見阿伯對我擺擺手,一臉示意要我趕快回家的表情。
「厚,阿伯!」
「肖年耶,能見到你我很高興,抹吃趁燒嘿。(台)」阿伯邊說著,順手挽起衣袖,開始準備收拾攤子了。
我只好對著阿伯笑了笑,向他道了聲謝謝,便轉往便利商店的方向走去。
「肖年耶!」突然,阿伯叫住了我。
我轉頭望著阿伯,只見阿伯的臉上露出了靦腆的笑容,不太好意思的說「嘸啦,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我對著阿伯揮了揮手,向他道別。
在這氣溫只有十幾度的寒夜裡,除了我那床棉被之外,就屬阿伯給我的暖意最踏實。
回程,我買了一杯阿伯最愛的珍珠奶茶,在路過阿伯的鹽酥雞攤位時,卻沒見著阿伯的人影。
「哇,阿伯的動作也太快了吧,只是買個啤酒的時間,攤子就收好了!」
我左顧右盼的四處張望著,或許阿伯才剛走吧。
路燈昏暗的光線灑落在鹽酥雞的攤位上,滿是灰塵的帆布讓我感到有股說不出的怪異。
回到房裡,我打開了許久沒用的電腦,在桌上攤開了溢著熱氣的鹽酥雞紙袋,又擺上了一手啤酒,如果再配上一部好電影,那就真的是實實在在的享受。
「嘖嘖嘖,人生啊!」好久沒有這麼愜意了。
叮咚!叮咚!
門鈴聲?
迷迷糊糊,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睡著的,睜開眼,已經是下午一點半了。
窗外的天空陰陰暗暗,正淅瀝嘩啦的下著大雨。
剛才…好像有門鈴聲?
家人昨天才出國的,會是誰啊?
打開了大門,沒人?是誰按錯了嗎?
關上了大門,我再度回到房裡。
「shit!什麼味道?」
亂七八糟的空酒罐與鹽酥雞的廚餘,交雜著汗臭使房裡的氣味變得很像…
很像…腐肉?總之,就是非常的噁心難聞。
暗自在心裡罵了幾句髒話之後,我只好摸著鼻子開始默默的收拾自己搞出來的殘局。
忙了好一陣子,我到浴室沖了個舒服的熱水澡。
當我擦去鏡子上的霧氣時,突然,一張血淋淋的臉,映在應該屬於我的臉上。
那張臉,血肉模糊得極其恐怖,五官扭曲到無法分辨原來該有的樣子。
一個驚嚇,眼花了吧?
閉眼,再睜眼,鏡子裡只有自己,看來真的是眼花了!
離開了浴室,我泡了碗麵,一點也不把剛才那幻覺般的影像當一回事。
窩進房裡,翻出了我的武俠小說,一邊吃著麵,一邊啃著我的華山論劍。
乓!一陣玻璃碎裂的聲音,嚇了我好大一跳,趕忙跑到客廳看個究竟。
「shit!」
這一看,只能用傻眼來形容了。
客廳那座強化玻璃的茶几怎麼突然破了?
是因為…冷縮熱脹?胡扯!
還是因為…重壓?說不定剛才有蟑螂爬過!
慘了,這下該怎麼跟爸媽交代?說什麼都很牽強!
剛才在浴室裡見到的恐怖影像,瞬間劃過我的腦海。
難不成是因為有鬼!
白痴,自己嚇自己。
可是客廳沒有人,桌子沒有理由平白無故的自己破掉呀!
疑問,回應我的只有滴滴答答的雨聲,以及越發陰暗的天空。
靠,越想越毛。
我動作迅速的把碎了一地的玻璃收拾好,拿起了手機,撥了電話給好友大白。
「喂?」通了。
「喂!大白哦…」
「嗯?」
「媽的,你還在睡哦?」
「幹嘛啊?」
「喂,我跟你講,剛很玄…」
嘟嘟嘟…大白掛掉了電話!
「靠,敢掛我電話。」我不死心的再撥了一次大白的電話。
嘟嘟嘟…電話被切掉了。
「媽的,嫌我吵是吧!算了,找小偉。」
按著按鍵,找到了小偉的電話。
嘟嘟嘟…電話又被切。
「幹,小偉八成又上哪去把妹了,還說是哥兒們,要找人的時候連個屁都沒有。」
接連撥打了兩通電話都找不到人,光顧著氣,倒也不怕了。
至於剛才的現象,若要給個合理的解釋,那就當作是熬夜看電影,外加喝醉酒所產生的幻覺吧。
在自己家裡還能有什麼,我才是主人,頂多叫鬼滾出去唄!
既然沒人理,也懶得想那麼多,拋下了手機,我從冰箱搬出了啤酒,再度回到我那溫暖的被窩,繼續看著我的武俠小說。
這假放了三天,雨也下了三天,家人還沒回國,但是我得回部隊了。
奇怪,不是過年連假嗎?
今天這班開往台東的自強號還真是異常的空蕩,這節車廂連我在內一共只有三個人。
其中一個是和我一樣要回部隊的軍人,而另一個則是個戴著斗笠的怪人。
雖然我們分別坐在不同的座位上,各自做著自己的事,但是那個戴著斗笠的怪人讓我很毛。
怎麼說?
戴斗笠的怪人上車後,他的斗笠沒有拿起來過,還刻意將斗笠壓低,讓人無法看清他的臉。
尤其是在他坐定位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動作了,維持了一個很固定的坐姿動也不動,整個就是怪。
我很想不去注意他,但他偏偏就坐在我看得見的位置,想不去在意還挺難的。
車程還要很久,我閉上眼睛拋開了斗笠怪人的影像,打算來個閉目養神,眼不見為淨。
「欸!」
突然有人在我的肩膀上輕拍了一下,我睜眼一看,是那個軍人。
「什麼事?」
「火車停在這個站很久了耶。」軍人指著窗外說。
我轉頭望向窗外,是個很陌生的車站。
「這是哪?」站牌上斑駁的字跡寫著「永安」。
「不知道啊,我不記得有這個站,火車停在這已經十五分鐘了。」軍人聳聳肩,一臉莫名奇妙的表情。
淡淡的薄霧籠罩著候車亭,站牌的燈箱忽明忽暗,昏暗迷濛的光暈,使整個車站迷漫著一股詭異的氣氛。
「要不要下車看看?」軍人提議。
儘管感覺不太對勁,但面子還是要顧,不能怕!
況且身旁還有個弟兄可以壯壯膽,探個究竟也無妨。
「好,去看看!」
我起身跟著軍人走在後頭,當我經過了斗笠怪人的身旁時,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我們一前一後的下了火車,左顧右盼的環視著車站。
走近一看,才看清站牌上的字跡原來寫的不是「永安」,而是「永遠安息」。
不尋常,有這個陌生車站不尋常!
我和軍人大吃一驚,慌了手腳,在我們都還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
「肖年耶。」
我和軍人不約而同的抬頭望向候車亭的屋簷,是剛才列車上的那個斗笠怪人。
不尋常,一個好端端的人怎麼會坐在屋簷上!
「能見到你我很高興!」
這是…阿伯的聲音!賣鹽酥雞的阿伯竟然出現在這裡,這是怎麼回事?
斗笠怪人輕輕的取下了斗笠,血肉模糊的臉上分不清五官,一顆眼珠還掛在眼眶外搖來晃去。
幹!我想我和軍人都很想逃,但是腿軟了根本走不動。
我轉頭想看軍人的反應,怎料軍人遽然腦漿四溢,臉上的皮肉像溶化般一塊塊的剝落。
我倒退了幾步,剎時攤軟在地,心臟不聽使喚的瘋狂跳動,撫著胸口,我摸到的是血淋淋的心臟。
瞬間,血水浸濕了衣褲,沿著四肢慢慢的滴落地面,坐在血泊之中,我驚恐的喘著氣。
「該上路了。」阿伯站起身,對著我和軍人招手。
「為什麼?」
我不懂,向來對我很好的阿伯,為什麼要這樣帶我走?
一份報紙,倏地掉落在我和軍人的面前,報上斗大的標題寫著「死亡車禍,三死十二傷」
死亡名單上印著三張照片,那正是我和軍人還有鹽酥雞阿伯的大頭照。
鈴…鈴…
「喂?」在桃園國際機場,一個正在笑鬧的女士接起了手機。
「請問是伍士其的家屬嗎?」
「是,請問你是?」女士收起了笑容問。
「這裡是仁人醫院,剛才高速公路上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伍士其在到醫之前就已經死亡了,麻煩家屬先過來醫院一趟,這裡的地址是…」電話那頭說著。
凌晨兩點,伍士其的家人剛從醫院回家,散落一地的行李,任何人都沒有心情整理。
伍士其的父母攤坐在沙發上痛哭,怎麼好端端的孩子放個假,卻在返家的路上發生了這種事。
其他的親朋好友也紛紛打電話來確認,到底電視上報導的那個人,是不是就是他們所認識的伍士其。
叮咚!叮咚!
門鈴聲?
迷迷糊糊,家人們哭了一整晚,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睡著的,睜開眼,已經下午一點半了。
窗外的天空陰陰暗暗,正淅瀝嘩啦的下著大雨。
伍士其的爸爸打開了門,來的客人是伍士其的好友大白和小偉。
「伯父,我看到新聞了。」大白有些哽咽,而一旁的小偉表情默然。
「你們先坐吧。」伯父一夜沒睡的倦容,提醒了大白此次前來的用意。
「伯父,看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幫得上忙的,您儘管說就是了。」大白和小偉一臉認真,任誰也不忍推辭。
「你們先去士其的房間,替他找張照片吧。」伍士其的爸爸低著頭,壓抑著悲痛的情緒,輕輕的撫著紅腫的雙眼。
「欸,什麼味道?」大白拉著小偉推開了伍士其的房門,一股腐敗的氣味隨之襲來。
「好臭,開點窗吧。」小偉拉開了窗戶,試著讓房裡透點氣。
「大白你看,伯父把電腦都開好了,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用的照片。」小偉盯著發光的螢幕,幫忙搜尋著電腦裡的相片檔案。
大白也開始著手翻找著書櫃裡的相本、儲存相片的記憶卡或光碟片。
乓!一陣玻璃碎裂的聲音,嚇了大白和小偉好大一跳,兩人趕忙跑到客廳看個究竟。
「怎麼回事?」客廳那座強化玻璃的茶几碎了一地,伯母正扶著倒在一旁的伯父。
「沒事沒事,本來要收拾行李的,一陣頭暈就把桌子給砸破了。」伍士其的爸爸摀著額頭,似乎沒辦法站起身。
「伯父,我扶你到房裡休息一下吧。」小偉見狀立即上前攙扶,大白也迅速的拿起了掃帚,幫忙清掃著玻璃破片。
忙了好一陣子,大白和小偉一同在沙發上坐下來休息。
「欸,怎麼會這樣。」小偉揉著發酸的雙眼說。
手機鈴聲突然響起,大白嘆了口氣,有氣無力的接起了電話。
「喂?」
「…」
「嗯?」
「…」
「幹嘛啊?」
「…」
大白一臉不爽的掛掉了電話。
「誰啊?」小偉問。
「阿災,打來還不講話。」大白按著通聯紀錄查找著剛才的來電。
「怎樣?」小偉一臉好奇的湊上前。
「是…是…」在看到來電紀錄的剎那,大白的臉,瞬間沒了血色。
手機鈴聲再度響起,螢幕上的來電顯示著「伍士其」,大白抖著手,按掉了通話,嚇得把手機丟到一旁。
「怎麼會,阿其的手機不是已經…」話才說一半,這回換小偉的手機鈴聲響起。
「怎麼辦,這次打給我了…」小偉嚇得切掉了電話,兩人面面相覷的愣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