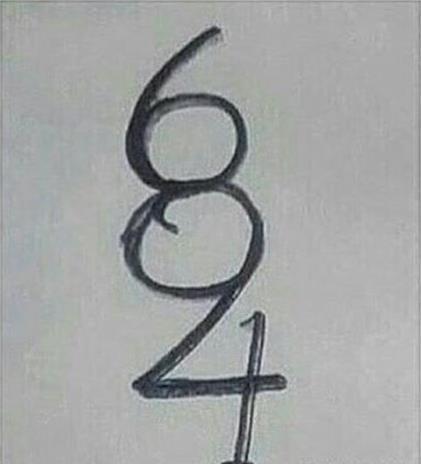散文/夜行高雄
我的一位高中同學,上大學以後就讀東吳大學中文系。她在士林,而我在景美。從世新大學步行至景美捷運站約十五分鐘;我通常只需要十分鐘。大一那年,松山線尚未通車,從景美到士林,我可以閉上眼,下一次睜開剛好到了。過頭亦不要緊,捷運是一種這麼容忍散漫與過失的交通工具。到士林以後轉公車,約十分鐘,過一道馬路,據說,那是全台北最長的一個紅燈。這又是很久以後不經常去了才知道的事。一趟接近二個小時的路程,又怎麼會去計較一個紅燈一百秒二百秒呢?
某一個夜晚我想起她,已是數月來才想起這麼一次。我問道,「週末有時間嗎?」她答,「我和家人出國玩。明天要走了,下週才回來。」當時的我有股急迫急切的動能:我現在就要見到這個人!她就要離開了,現在就要見到這個人!「明天一早八點在小港機場的班機。」她說。當晚我下訂最後一班南下的高鐵,抵達車站的時候比即時要早一些。那張車票是那時的我唯一的奢侈品。高鐵緩緩發動,我在想:不知道抵達高雄的時候還能趕上末班捷運嗎?車廂中望外黑漆漆的,看不出走了有多遠。不禁又想:一車廂裡,乘同一列末班車,一座島的頭頂滑落到腳趾頭,都是為些什麼原因呢?我這時難免有種自喜之情:從這節車廂數起,往兩邊數,不曉得延伸多遙遠……不會有另一個像我一樣的人。
下列車後許多人奔跑起來。站務員高聲呼喊:「最後一班捷運五分鐘後即將發車,欲搭乘的乘客請盡速前往。」趕上了。可是我的雙腿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奔跑起來。默默走到建築物外頭,月亮高高懸在頭頂上,腦袋得整個地仰起來。現在是子時,是半夜三更,天色最黑、最暗的時候,也是月亮懸得最高、照耀最廣闊。我查了往機場的路線:十六公里,三個半小時,我的腳程快一些,試著三小時內抵達吧!路面上昏昏沉沉,路燈,便利商店透出的燈光,不至於一個人也沒有。走不多遠,路邊計程車司機問需要載上一程嗎?我告訴他,「沒有關係,不用。」他說,「這麼晚了,很遠的。」大概是司機職業病吧,我心想──你要是知道我去哪裡,不會只是說「很遠」的。
這麼深的夜裡,紅綠燈喪失意義。我依然遵守交通規則。一名醉漢提一支酒瓶在後方跟上來,與我攀談。我沒有說明自己的目的地,他也不問。他說的都是自己的事,如今我已忘了。也許當時太在乎自己的事。也許當時候太晚,對任何人都充滿戒心。我曉得他是好人。然而當他提著酒瓶,我便不想與他走在一起。
我是相當清醒的。當我經過一座形貌極其工業化的天橋,橫跨快速道路。橋上牽引鋼筋,滿佈線路,貼一警示告牌:請注意高壓電,危險。當我路經一長長深遠不見盡頭看似荒廢其實休眠的市場,風吹在前,時而在後,似埋伏,似尾行。狗兒咆哮,那反而是一陣生氣;然而叫得久了,叫得遠了……顯得荒涼。當我離開市場,已經有人拉起鐵門,備料,做準備工作。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西部濱海高速公路,路面寬闊,中央分隔島是一道長長的花圃。花圃裡沒有花,只有醜不拉嘰的滿地亂草、崎嶇的岩地。我不禁想到這好像形容自己目前的處境,我劇本裡的畸零地,那些荒煙漫草像垃圾吃垃圾大南國的孩子一樣,無節制生育底下總有那不幸的競爭力不足,還未長成便夭折。我的劇本中,便像是那濱海公路上滿地亂草中扶不起一朵夭折的花。
到達機場時是三點半,和導航預估的時間相差不多,大概是在濱海公路上的岩地耽擱太久了,也或者就是走累了。我沒有出過國,離島也沒有,一生中第一次到機場就是第一個到的。大廳裡黑壓壓,廁所也是,只有飲水機的燈光,櫃檯的電子告示板。走到候機區,我找了一個最不起眼的位置,靠著椅子睡著了。
接近五點時候,漸漸地燈亮了,周遭的人聲一波一波浪一般淹上來,睜眼的時候到處都是人了。不久收到她的訊息:到了。我花上幾分鐘尋找到她,與她的家人們。她向家人告假,附近找位置坐下來。「我們只有十五分鐘。」她不熱情。我也顯得冷靜。「好的。」我說。然後我們聊起來。十五分鐘過後,在原地分手。她回頭尋找自己的家人;望著直到她離開。我搭上捷運,轉車客運,一路上再也沒有醒來,熟睡回到台北。
回台北後依然在原來的生活圈裡,修改劇本,在演員面前抬不起頭來。數月後,社團公演,我在觀眾席睡著了,到謝幕的時候從掌聲中醒過來。收台的時候有社員告訴我,認為劇本寫得很棒。我不確定她看見什麼;因為我自己睡著了。作為一介編劇、創作者,有讀者、有觀眾,總是好事,我於是不過問,謝謝她吧。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