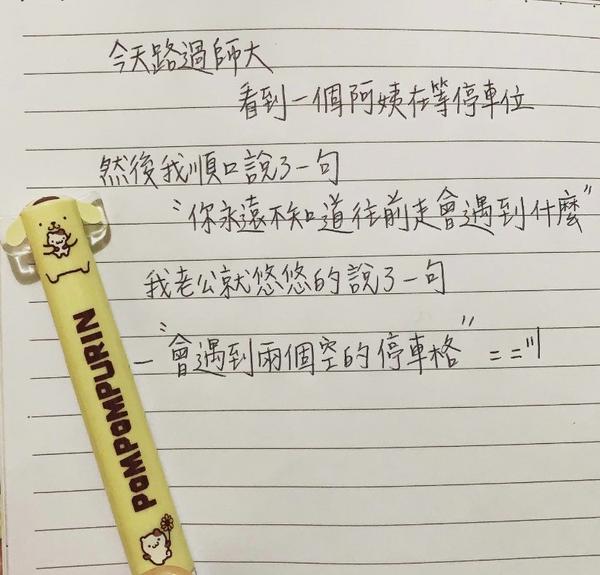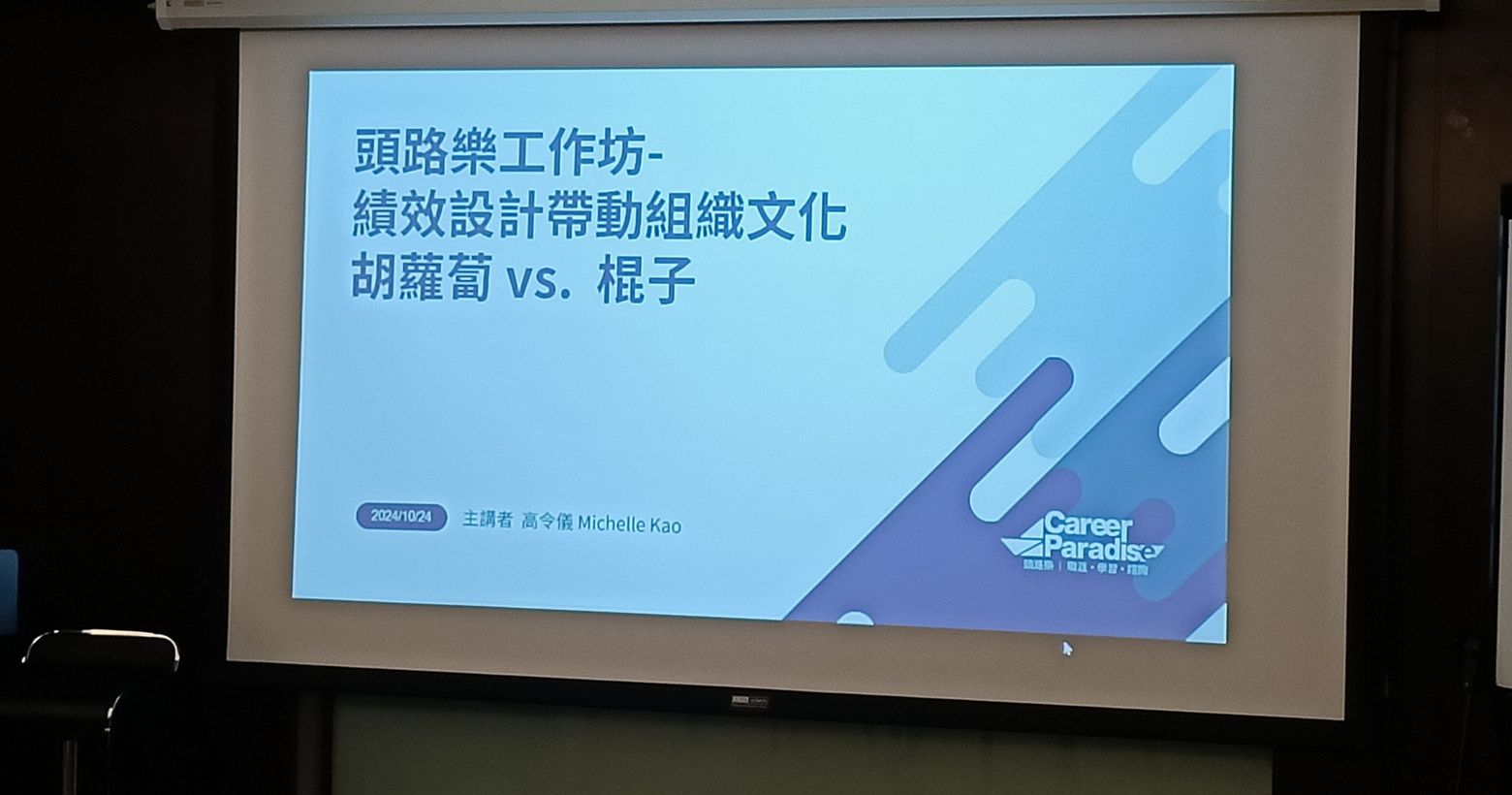關於昨日/今日
-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是能清楚知道再次靠近某些特定人事物、主題時,是會讓自己難受的。這樣的我們懷有篤定,卻偶爾也篤定地知道自己仍會無法克制也不顧後果地一再觸碰它。表面溫暖柔情的它,實質承載了可以撕裂我們情緒的銳利。這行為背後有很多可能因素,事實便是我們更遍體鱗傷,沒有走向更好,而是變得更不好了。
-
昨日:
我清楚知道在大篇幅書寫特定主題時,自己會陷入很糟糕的狀態裡,卻時常仍執意要這麼做。我無法因為顧及爾後將隨之而來的悲痛,而去強要自己捨棄書寫那些主題,我做不到。大概是因為生命的重量幾乎都是它們施予的,而若選擇了忽視這些重量,我的生命裡便不再有能讓自己站穩腳步的一小塊基石。像緩緩融化的浮冰,終有一日我會像融冰成水一樣,化進茫茫裡,然後下沉、下沉、再下沉,沉進那黑得什麼都看不見的海底,甚至或許沒有海底,得一直感受著下沉。所以儘管痛苦,我還是知道自己需要它們,很矛盾、很戲謔的,需要它們。
可怕的地方在於,每一次的書寫必須用力的感受那些觸碰,感受那些因為觸碰難過而有的顫抖。「人走了以後是不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就會漸漸失去形狀、顏色、重量、聲音?」他離開以後我最常問也最想知道的,是他在哪裡,究竟在哪裡。心裡不知道他身在何處的惶恐是極為裸露也無處可藏的,那不在感已經啃食了一大部分的心靈,也持續咀嚼心靈的神經,痛得透徹亦深切。「那不在感逐漸在我心中快速膨脹,並激烈地侵蝕我的意識。那不在感把過去應該曾經明確存在過的存在感壓倒,並貪婪地吞食殆盡。」《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裡的這段話能夠貼切地形容我的感受。不在感讓我的想念變得無處可以寄託,沒有世間存在可以承載,不覺得荒涼嗎?為什麼想念起來時,不可以是溫暖的微笑著,而要是荒涼的痛哭著呢?
檯燈切換到復古黃燈,微弱溫柔的光源和那首聽著總會淚流不止的歌化在一起,迷茫視線裡多麼渴望可以看見你的輪廓。可在無際的氾濫裡,我始終只看得見自己,孤身,墜落。側躺縮起身子,嬰兒在母胎中的姿勢就像回歸自然的擁抱;如果我不覺得自己能夠被誰拯救,那就暫時讓自己這樣被擁抱吧。
-
今日:
早晨來臨,醒來的原因不是什麼柔和晨光照耀,時間點純粹地像一點意義也沒有的存在。眼皮腫得壓縮了視線,檯燈和音樂都開了播了一整晚。嗓子沙啞,但我不記得自己有在淚海中嘶吼;我的眼淚總是靜默的。
下午終於出去走走,還騎了腳踏車,是來台北後第一次騎腳踏車。小時候是他教我的呢。想著就看到很多畫面,發覺不在感瞬間被抹煞,而他曾經存在過的事實是嵌在我的生命軸上,扎扎實實地嵌著。他沒有去了哪裡,更沒有消失,因為回頭便能發現他無所不在。眼淚跟雨水打在一塊,可我在微笑,因為忽然覺得找到他,更快要看見他了。
回到宿舍時鞋頭被雨水浸濕,襪子也早已濕透了。外頭細雨冰涼,可是心好暖、好暖。你感覺的到嗎,因你而暖和的心,無時無刻都充斥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