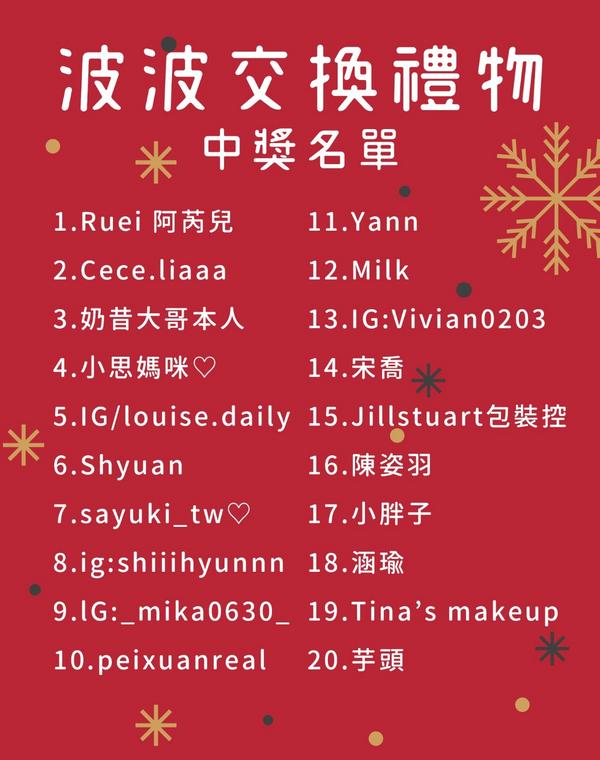關於小盒子
-
有些東西或許終究是自己一輩子所不能擁有的,或說要在死亡的前一刻才能獲得。
-
走在黑壓壓的長廊,還沒到真正的門口就被震耳的聲量侵襲,不過真的走進去以後,音量已經達到可以和手上裝著劣質酒水的硬質塑膠杯產生他們之間以我作為媒介卻沒問過本人意願的共鳴。眼前是一間小小的房間,看不太到四邊的牆壁,僅有前方大屏幕上的霓光色字體跳動,讓我知道那是前方的底線,可另外三邊都是未知,有礙於那在入口就已經分好了的階級,如同社會本身那嘗試撤除卻始終洗刷不掉的,分類。因此我們移動的區間多在最核心的下一個層次到底線前的邊陲,視自己與玩伴的狀態來移動、改變位置。偶爾在我口中所謂底線前的邊陲時,會有那些踰越自己地盤的人從耳邊或背後輕輕給了邀約,一概拒絕,這是我那天走進入口前立下的原則,我對他搖了搖手。然而,把視線從最佔據存在重量的事物中暫時抽離,其實旁邊的小小角落有著很多的故事,角色們演給自己的劇場,投入到根本不知有我這個觀眾的存在。
在那個小盒子裡,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擁有掏空人主體性與使某些人把自己物件化的魔力。眼前的人們流為聲量的囚犯,而酒水則是間諜電影裡色誘目標人物的角色。大略在換過第三個硬質塑膠杯後,忽然覺得自己也無可避免的、虛弱地即將被聲量制約。不過不是那種激烈的跳動,是癱軟地直接就地求饒。慢慢旋轉的世界扭開眼淚的瓶蓋,灑出來的時候沒落在音樂節奏點上,亂七八糟地、自我地,氾濫。我在他耳邊說聲想去廁所,不用陪我去,好好待在此地回頭才能找到人。他狀態已經不太好,眼神迷茫、兩眼渙散,卻依然堅決要陪著我。然後穿越過一叢一叢扭動的人群,在有微弱紅光—整個空間陰暗到連鏡子裡的自己都看不到的時候,我徹底地再也跩拉不住內心在清醒時刻要壓抑的一切的氾濫潰堤,靠在他的肩膀上,用盡全力的大哭,而那已經是不知道最後一次是幾年前的那種,有聲音的哭。這些年來我連哭都迫使自己要是無聲的,告訴自己眼淚要是靜默的,而或許在那個聲量可以侵蝕你所見一切存在的空間裡,我真的放下某些苛刻的限制,終於寬容地對待自己壓抑著的情緒。不過大概是因為我知道那裏不會有真正在意自己的人聽見與看見,所以綑綁才能稍稍卸下吧。就這樣趴在他的肩膀,在他的擁抱裡用盡力氣大哭了約莫半個小時吧,沒力氣了,我們才走回小盒子的主要空間裡。他說,不要這麼壓抑好嗎,我想要你開心,用那無法對焦的雙眼看著我臉上的某個部位。我笑了笑,心裡很感謝,就連他已經瀕臨醉死,還是這麼地照顧我的情緒感受。
後來真的不知道我們三個是怎麼走出小盒子的,路線記憶已經極度模糊,只記得有人一直嚷嚷說要去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誠品,然後還在我耳邊不停說教說就是因為沒有把身體徹底交給音樂才會哭。妳為什麼哭呢?他說。後來出了建築物,我們就癱軟地坐在人行道旁的木條椅上,而且事後舊地重返才發覺恰巧是一個仰頭就能欣賞101的完美角度。他繼續滔滔不絕用英文講了長篇大論,到現在我只隱隱約約記得有logos、you have to…等等字詞頻繁出現。不過他會這樣也是為了照顧我的哭泣,他們兩個就算已經踩在醉死的臨界點還是用力的給我溫暖。這絕對會是以後回想起那天經歷時總帶著微笑也滿懷感謝的原因,對於我大學時期這兩個根本可以說是現實生活裡,可觸及的距離裡最重要的人。我們待處在一起總是在創造故事,創造那些他所謂以後可以告訴滿堂兒孫們的故事。後續有一些混亂發生,譬若相繼經歷關於酒水再回到體外狀態的過程,抑或失溫發抖,又或者...嗯,總之就是一些不堪回首卻又荒唐好笑的生命插曲。
有時候覺得我們湊在一起的時候不斷地在突破生活不真實感的極限。昨夜今晨像場夢,記憶很破碎,連碎片本身都有許多缺口。但能跟你們待處在一起,我感受得到和你們一起揮霍等於珍惜的滿足。不過,這次的行程我們三人有共識絕對不會再有第二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