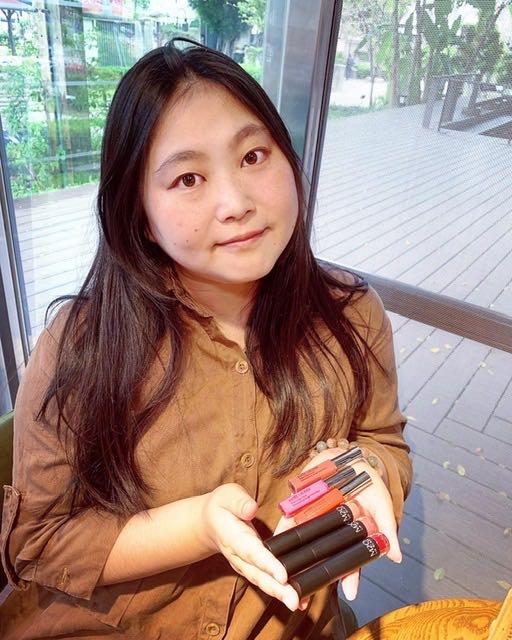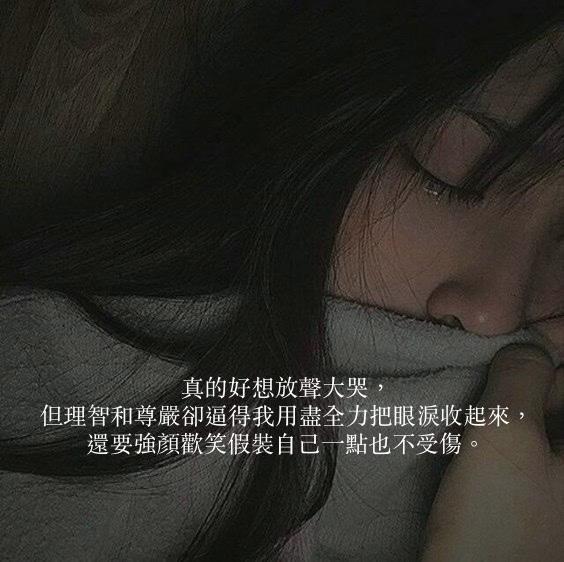關於回家
-
一出隧道,陽光撲面而來,有點刺眼,有點炙熱。是不是回家的心,除了雀躍也要綁上很多溫暖跟明亮呢,跟那冬陽一樣。宜蘭很久很久沒有這樣燦爛明媚了吧,我心想。眯起眼看著好久不見的家鄉,看著波光粼粼的片片水田,看著這個世界在出了隧道以後遼闊起來的樣貌。「對不起我這麼久沒回來。」心底忽然冒出這句話,對著眼前好熟悉的地方說道。那瞬間忽然懷疑起自己是不是其實是喜歡回家的,而非如平時總堅決又無情對著別人那「家裡很近可為什麼久久才回家一次」的提問給出的答案一樣冷漠。眯眼看窗外,心裡緩緩跑著質疑跟審查的程序。而耳機裡正巧播到Castle On The Hill,一首關於童年與家鄉的歌。
-
每次回家,只要時間跟身體狀況允許,都會去練合氣道。雖然通常都是隔了兩個月之久才去,但年近古稀(應該超過了)的老教練看到我時總是很開心。這週六去了課堂,回到那個從小五就開始每週到訪的道館,熟悉裡不敵時間走過的力量,看得見一點一點脆化、老去的痕跡,環境是,事物是,人也是。小時候其實很抗拒學合氣道,起初總覺得委屈,因為迫於父母壓力而必須學習那些我所排斥的-儘管他們的要求是出於希望我能知道怎麼保護自己。那麼好幾年我就是極其不甘願地上著每一堂課,而心裡真正能夠接受的時間點,要推到升段考試的前夕,也大略已經學了五、六年之久。那些拚命練習的日子裡,真切有獲得一些感動和體會,最後也確實順利取得初段,也和一些小朋友培養出革命情感。取得段位是很重要的象徵,除了技巧與能力上的肯定,更多的象徵了我越過自己心理一直以來有著的排斥帶來的阻礙,最後還能用乾淨的心態與視野來看待這項武術,重新學習,並慢慢喜歡。
「我會老,你們不能忘記吶⋯」老教練在示範動作的時候冒出這句感慨之言,這是從小到大的我第一次聽見他說出這句話。這週六的課堂他頻頻叨念著希望我們不要流失掉這個系統上最強的兵器,要好好保存下來,兩個小時的課堂他就糊糊地唸了三、四次。我驚覺眼前的老教練,或許形體上因為是練武之人難顯蒼老之色-這八、九年來看起來都是一樣硬朗、面色紅潤,但然仍不敵歲月推進之快,實質上老去的感受仍然讓他有壓力,因為他,是有使命的生命體。豁然明白近幾年來為什麼他總是那麼努力在參加各種比賽跟推廣會,明明這不是他原先的作風吶!看著眼前示範動作的老師,我眼眶泛淚,此時此刻又更強烈想要說一聲:「對不起我這麼久沒回來。」生命裡總是有那些無論多麼努力也始終無法完整地全部轉移傳承的部分。很多事物的存在始終會隨著生命的終結而消失,同時在他人記憶裡的佔比也會漸漸變少,最後徹底淡出。然而,某些部分的他或許被記住了,但那個被記住的,所謂「永遠留在世人心裡」的他,從來從來就不是完整的、飽滿的他啊。總有一些部分隨著生命的終結也一同死去了,而那些部分其實根本幾近於整個他了啊。
課堂結束後,在下樓梯之前,離開這個慢慢脆化、老去的空間之前,我停下腳步再次好好看看它。老教練看著我,笑到瞇起眼睛說:「有空要再多回來上課喔!」我大力的點點頭,想著眼前的他這些年來對我的照顧與教導,在生命裡是多麼有份量。
-
然而,不回家的我或許只是在避開自我揭露的風險-深怕走回滿是連結的地方會遭到不可掌握、不可預期的觸碰。或許不回家也是以為可以避免面對那些已經縫在這個地方的傷痛痕跡,不走進真的能不感受到嗎?還是只是因為不願意感受到更多呢?或者不回家只是單單因為喜歡一個人或需要一個人嗎?以為不回到房間就不會翻閱書櫃裡塵封的那令人回憶起傷痛的作文嗎?但明明我在房間以外的地方還是一直寫一直想啊。自我審查的程序丟出了很多疑問,但我始終沒有確切的答案,對於我不回家的罪名。但不回家的罪名不能嵌上我不喜歡這個地方的指控。儘管家或許不是歸屬,但我知道我愛這個家,也喜歡我的家鄉。其實從小心底就有一股莫名的力量總嘗試告訴我些什麼,大概還小,所以不明白,直到後來才能用清楚的文字去解釋那種感覺:世界在等待我去尋找那個「真正」有歸屬的地方。這也是為什麼我把「歸屬」放在未來的時間軸上了,我深深相信它在那個時空空間裡,而找到它是我作為一個生命體的使命。
現在每次從台北回宜蘭,我都能強烈感受到自己對於這種遼闊的依戀-儘管我依然堅持不將其稱之為歸屬。可是,我真切地知道自己對這塊土地是有很多感情的。
大城市啊,真的太擠了。視野狹隘,空氣渾濁,我都快忘了自己是山和海孕育出的孩子。但還好,每次越過那座山以後,我就會想起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