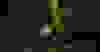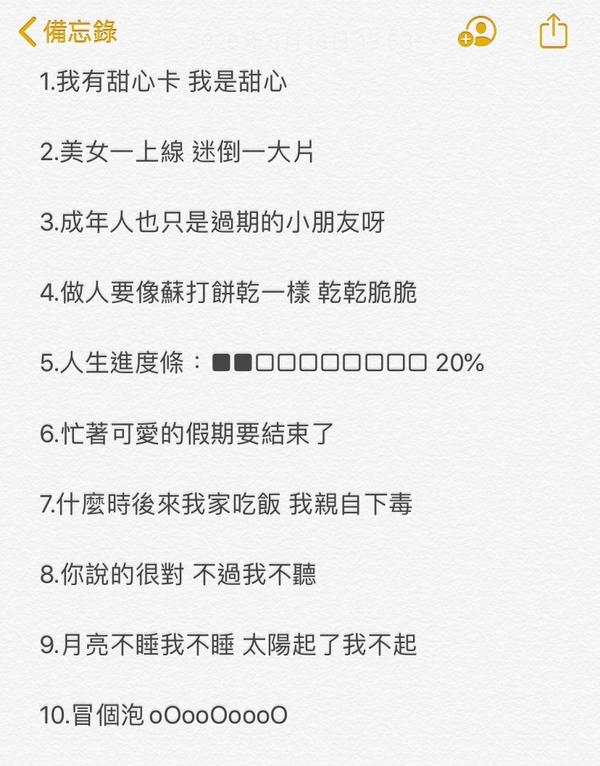與人為善/時下的性
(在這樣的時刻談論性,男性與女性。
謝盈萱最近在臉書分享了一段自己租屋處的生活。
留言處有人說,溫暖,溫情,溫柔。我是理解的。我也知道這篇貼文要說什麼;但我其實是看得很難過的。也不見得是為了裏頭避開目光的男生感到難過,只是我有很強烈的帶入感,為了那種戰兢,高空走索。我又再一次感到那種莫須有的罪名,被提醒的,不知何處來的注視,目光,那是在我進入了一個女性的住所,整個人的警鈴響作到最大,四周潛伏,危險勿碰,像電流急急棒,視線無處滑走。掛在陽台的內衣,那是一個很好的隱喻。如果是一個女性的衣物,做為一個有意識(原罪)的男性,會有一種避開的反射,凝視就是侵犯。如果是一個男性的衣物,內衣褲高掛在陽台,女性進入。女性也會避開;但那不一樣。女性不希望男性見到自己的衣物,因為那是隱私,感到羞恥(這裡是我自己的判斷);男性不希望女性見到自己的內衣物,那是有一種猥褻的擔憂(不是猥褻罪)。這樣的差異,正是很恰好地反映了男性長期作為性的壓迫者的事實。而這樣的事實,也同樣壓迫著同樣作為男性的不作為者。這樣的不作為,不僅僅是犯罪的不作為,而且是會被指著鼻子罵道,「沒有人是局外人」,的不作為。
另外說到文學上的女性意識的書寫。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裡已經說到,女性「用力」書寫自己的艱困是其作品的致命傷(當然這很容易被誤釋)。這反映的是男性作為壓迫者的文學背景。同樣的,男性在女性議題中的書寫,經常犯的毛病也是「用力」書寫男性的罪惡,尤其是別的男性的罪惡。女性用力地書寫自己的艱困是一種耽溺的煽情,積極地要人們相信(這是她們的困境)。男性用力地書寫他者(同胞)的罪名,是一種切割,劃清界線,積極地要人們相信自己的清白(這也是他們的困境)。這兩者其一,都反映了女性做為性的弱勢者的事實。只要男性或女性仍然在用力地書寫,(就說明)這項問題還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