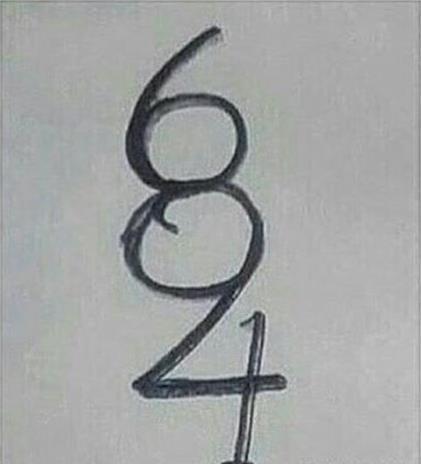關於差異時空裡的共感
不同時間軸上的,在有著相似氛圍的環境裡,時常帶來一種超越時空的共感。在那個沈寂下來的片刻,我忽然明白自己為何對於此時此刻待處的空間越發感到不自在,甚至偶爾有著幾近窒息的感受。對於那在同一團體空間裡,關係的遠近與濃淡的有所變化,所帶來的負擔。大概是記憶裡的傷害在這時若隱若現。「從來沒有什麼是可以在過去以後真的完全消失的。」如果沒有變化,打從一開始就是疏離,那我也不會有這種感受。改變彷彿時時刻刻都在提醒我,關於那些從十一年前開始的噩耗,持續了七年,儘管之中有兩年左右的空檔。可那也沒真的讓我好過一點。
多數時候,記憶都是這樣如鬼魂般縈繞。Haunted。被記著的,潛意識的,都魂縈。差別只是能不能看見,能不能解構,最後被自己重新詮釋。對我來說,能夠如此就是一種痊癒了。從來不應該期待可以恢復到原先的無損。從來不應該認為那樣才是痊癒。Unobtainable。
這讓我回想起先前相繼發生的,關於時間感(似巧合的)記憶的經驗-不同時空裡的部分共感。其一關於他,其二關於她。
一:2019.10
那天莫名地低落,停滯時眼淚隨便都能泌溢,卻又必須(應該說習慣性地)在狀態裡撐起剛強,除了緊繃地憋忍,也別無他法。那天卻異常地不如平時有韌性,剛強的表面過度膨脹因而炸裂,躲在廁所裡把體內所有看似沒由來也莫名的情緒碎片四射而出。傷得那個空間體無完膚。包括自己。但是這種重傷變向帶來一種紓緩。意圖迫使自己把被眼淚沖蝕至碎塊漫漶的靈魂收拾回癱軟的軀體,重新站起身,前幾次卻頻頻失敗。從來沒有想過能親眼見證自己如此失控的一片狼藉。
然後啊,在某個隨意滑著手機翻看日曆的片刻,沒來由也莫名的那些,剎那間都明朗也具名。「重陽節。」正諷刺地是他第二個忌日。
「細胞好像清楚地、有時間性地記得了所有事情的發生。」「抑制是一種防衛機制。那些不能被超我承受的事物被堆放進潛意識裡了。」原來細胞記憶的藉口美化了我的這些痛。
Your absence has gone through me.
Like thread through a needle.
Everything I do is stitched with its color.
- W. S. Merwin
二:2020.07
明天是陪她去輸血的日子。
兩袋血的時間,沈默不語。當時第一次帶她去輸血,唯一的聲音是我播了她年代的歌,想著或許音樂能夠喚醒什麼。人們總是對音樂有著幻想跟期待。可有些幻想注定破滅,有些期待只能落空。兩年後仍然,一語不發。數不清用了多少眼淚填補那些少了對話的空洞。幸運的是那時還有他能在焦慮與未知中承接每個瞬間隨時可能墜落的我。而那段時間裡他從來沒有失手過。
想著想著,就找了當時紀錄的,參雜我們對話的心情感受。然後發現那天的日期,是兩年後的今天。一樣都是我陪著她去輸血的前一天。
這看似有點像純粹巧合,但實則不太可能那麼純粹。我卻也沒有辦法說服是完全地時間感記憶作用。也不打算說服。沒有足夠強穩的立場-潛意識的、無意識的,都沒有把握,甚至連我記得的,都不見得有。唯一有的,是清楚記得她兩次都多麼奮力而緊緊地掐握著我的手。「她好像記得你。」這一點又回到了沒有把握。
這些時間裡的遺留物,從過往被沾黏性地拖移到未來,整個生命軸上都染上了顏色。生命與時間綜合體的不可斷性-這個說法比起延續性更強調了之於此特性的無奈,把那些沉也悶的,不斷不斷地帶往下一個階段,直至軸的盡頭,我的終結。可其實我從來沒希望過這樣的運作模式能被改變或是割除。這種痛間接也直接的證明了些什麼。
Jacques Derrida提過毒、藥的一體兩面性,說古希臘文pharmakon同時代表毒藥和救藥。解構主義這麼拆解世界。那麼愛呢?我總是認為它的反身或對反是痛。因為有部分的自己依留在他們身上,所以疼了那塊我。有時候他們的痛也是因為那塊在我身上的他們自己。就算如此我也從來不曾想過要遺忘,從來沒有許過「如果能夠一覺醒來便徹底失去記憶」的這種願望。相反的,我要記得,用最深刻、最用力卻也最痛的方式記得。因為這些疼的感受把愛刻畫得好清楚、好清楚。
愛的反身或對反從來不是恨。因為愛不一定有恨,卻不證自明地有痛。差異時空裡的共感,追溯到最源頭、最本質性的那處,都是關於愛,或是反身地,由愛而生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