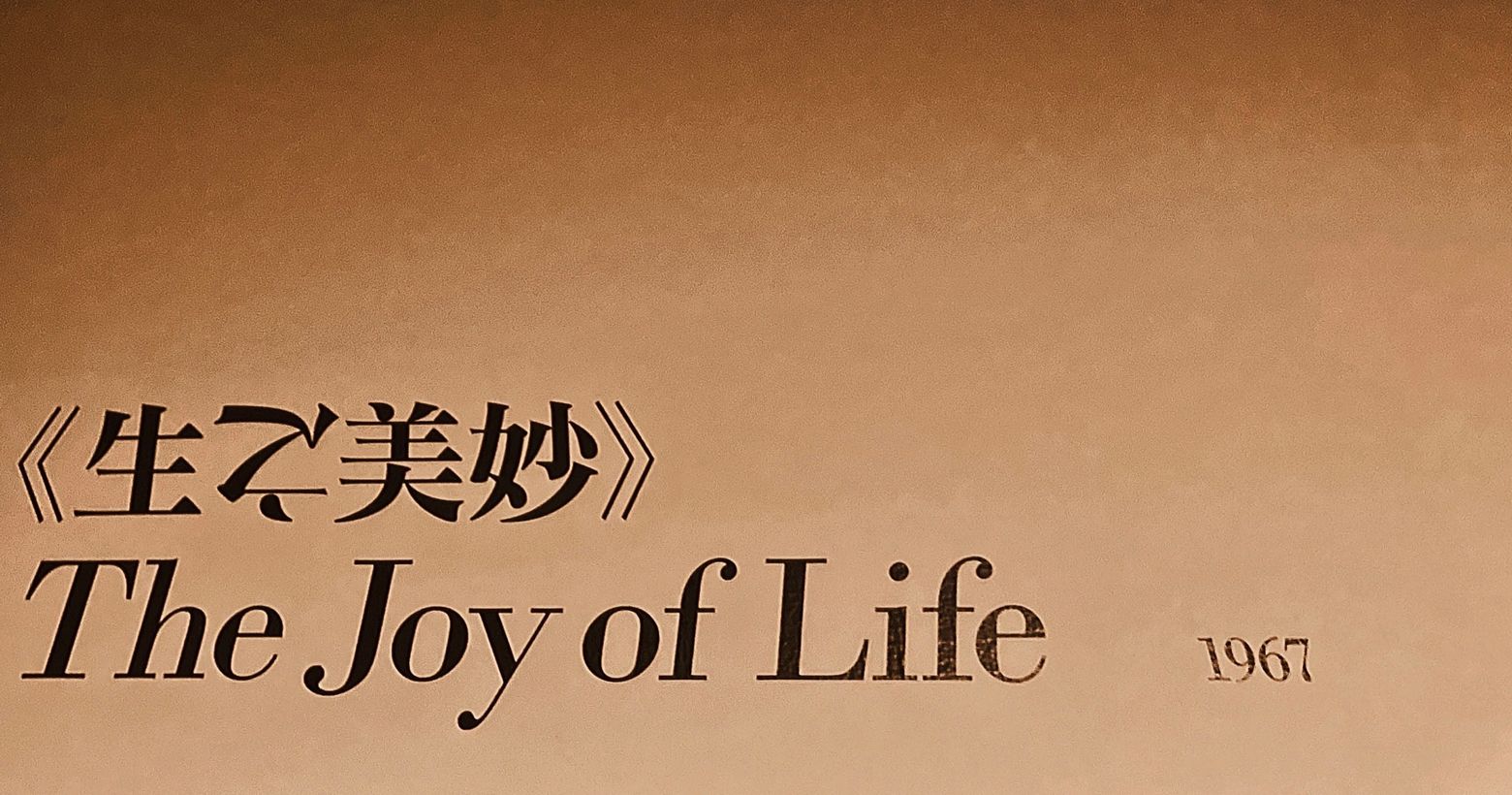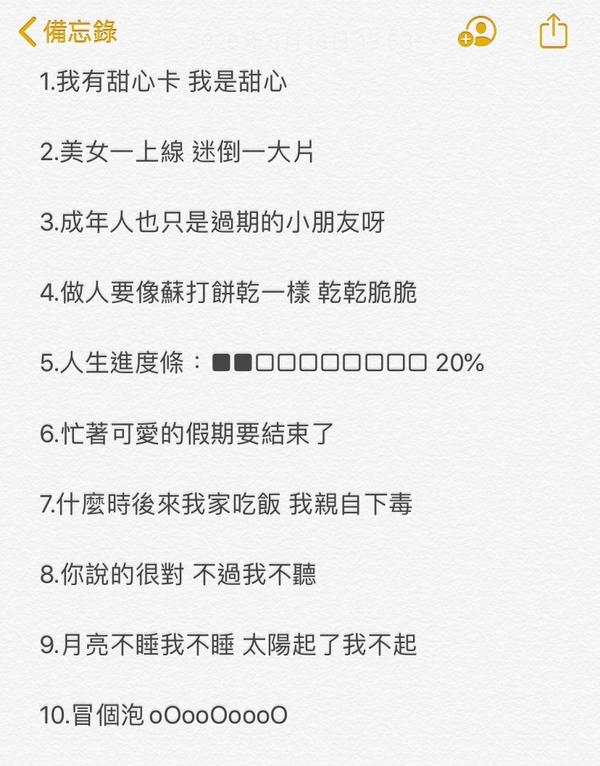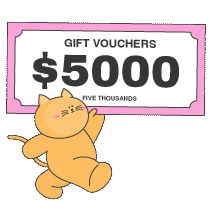關於J
至今我仍然想不起來自己是怎麼走過那段日子-不去責怪、不帶憎恨,甚至在所有人的告知與說服下,客觀事實應證著也無法洗去你認為她那擦肩而過的死應當究責於自身。爾後有一大段時間我的記憶很破碎,碎的原因不是被外力破壞,是太多大篇幅的空白與缺頁,僅剩的是零零落落的,殘留幾秒的眼淚,或者暴力。甚至遺落的片段都不能被自己正面地承認,唯獨清晰且正確地記得那天下午,在身邊有眾多人,而我卻再也無法隱忍而崩潰在身邊的人的懷裡用力顫抖與啜泣的樣子。那段記憶在過往是很痛的。可能殺了她的那些也忽然殺在了我身上。然而,除此之外其餘的只是一片死白。失去了那些記憶,是不是也不再有資格說自己痛了。沒有東西可以痛了,不是嗎。
那天,在坐上晚上十點多的公車回學校的路上,看到他傳來的訊息-前幾天才跟我說完話,以為處理好了什麼,女友卻吞藥自殺,可未遂,現在在醫院輸血。一剎那間,J迅速回到腦中-雖然她從來不曾離開過,可我想說的是關於她的那一切踉蹌地在我腦中重新站起來。但其實不會痛,我老早就沒有再感受到那些事情帶來的痛了。要說是壓抑作用嗎?可能真的是防衛機制吧。那時候甚至表現得像被撤換了記憶底片一樣。乾淨地,很寂寥。
他傳那則訊息給我的前幾天我們才剛談過話。想方設法解決他所面對的關係裡的龐大兩難與掙扎。雖然我們始終沒有成功避免些什麼。當時,我問了他一句話:「不覺得我們太自負了嗎?憑什麼覺得自己可以拯救他們。」起初的靠近都是覺得自己可以救起她們啊。可是最後我們不但沒有成功,某方面卻也成為她們的另一個傷口。想救人的時候,一不小心,也促成傷害。有時候真正殺死他的,是那自負的拯救。
我認真想過為什麼在望見洞口邊墜落的人會伸手。我想是相信拯救的力量,相信改變的可能。追根究柢是相信人。相信人所以擁有強意志能伸出那雙手,承受拉扯,遭遇掙扎。儘管如此,也依然一如始終地相信。然而,太多現實經驗與實例證明了人的孤身有多麼薄弱。正是為什麼多數時候那種相信總是失敗。自負帶來了拯救,可最後都是自毀。多數時候都是如此。拯救的行為本身自負,連背後的信仰驅使也是。自大也狂妄的相信人的本質與能力,那種啟蒙思想式的回到人本身,把人的可能性托抬到最高、至高的信仰,始終都太自不量力。
我們總是看不見自己有多渺小。膨脹也虛無的偌大裡頭殘酷地只有小。偌大的盲點遮蓋了自我的小與無力,而我們終究需要那樣自負的相信來躲避事實。那樣的空間像桎梏,人類的自我囚禁。極致單薄,也脆弱的不堪一擊。
爾後的J出現在每一個相似的故事裡。她成為一種象徵,不再屬於我生命軸上過往的單一角色。儘管現在的J已經生活順遂,可過往的她仍頻繁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故事裡。每當看見這樣故事色彩的人,我都會想起她。不痛也不沈地,帶上很多空白片段地,想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