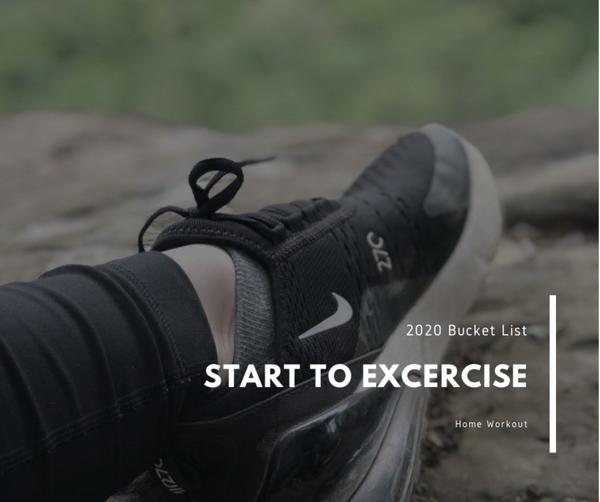小說:教授與他人之妻
洛水與羅清
羅清是我的老師—呂輝凱的妻子。將他尊為老師,其實我並沒有直接地師承於他。不過,沒有了他的提攜,我也就沒有今天副教授的位子。那天,我獨自一人乾待在研究室,眼前文獻上的一個個文字全像是天書一樣,我腦海中全是方姍姍。並非你所想的,我還沉浸在那一晚的憶幻之中,我在思考這毀滅性的錯誤是否會帶來甚麼不可預料的後果。將頭髮撥的紛亂,我決定不再枯坐在書桌前,關上燈,準備離開研究室。
月光照在了寂寞的廊道,一隻手從後方拍了拍我的肩。我轉頭看向手的主人,50來歲的年紀,頭髮卻已半禿,幾根固執的白髮不情願地浮貼在頭皮邊緣上。老成的臉孔戴著金絲邊眼鏡,洗的褪色的襯衫扎進西裝褲頭,頗符合服飾主人的年紀。除了腳上那雙突兀的可笑的Adidas的運動鞋以外,整個人儼然是個浸泡在象牙塔中,摧殘日久的大學教授。
「這麼巧?」呂輝凱用濫用以後摧折的嗓音問道。
「是老師啊,剛整理完,準備回家了」
「吃過飯了嗎?要不來我家吃吧?」
「不了,太麻煩老師您了」我回應。
「唉呀,說甚麼麻煩,完全不麻煩的,走吧。」
就這樣,我再一次的被老師給硬是邀請到他家中吃飯。老師家是間老式的透天厝,牆垣的裂痕在夜色下一張一合,哭訴著歲月的殘忍。我和他爬上4樓,手扶著漆上血紅色的老舊鐵扶手,跨過地震造成的裂縫,就著慘澹的黃色光線,打開了老師家的門。
走進門內,一名女子翹著腿,看著電視上無聊的節目。看似在發呆,眼神卻像是譏諷主持人的愚蠢。那女子便是羅清。老師邀我吃飯已不是先例,先前我早已見過了她,第一眼見到這女子,腦中會自然地就投射出一朵將要死去的山茶花。花瓣的邊緣已慢慢的凋萎,被深棕色的歲月侵蝕。坦白說,我猜不出她實際的年紀,她看來太過年輕了,和老師太過不稱,也許才四十初歲吧。
「死去哪裡?」女子用不帶感情的聲音說道。
「剛從彰師回來,遇到洛水,順道帶他回來吃飯」。
女子這才從電視上移開目光,我與她四目交會。她的臉僅略略施了些胭脂,些許的黃斑點綴在眼下,身穿件想扯回年輕美好的碎花裙。她有著與方姍姍一樣的雙眼,眼神有著方姍姍沒有的世故與老練。眼神交會過後,她熱情地招呼著我,完全將老師給晾在一旁,和先前幾次作客一樣,讓我頗為尷尬。老師大概也習慣了這樣的對待,並沒有多說些什麼。進了後廳,我們三人在後廳昏黃鎢絲燈的照射下動了筷。飯過中途,大概老師的興致來了吧,拿出了一瓶喝了一半的威士忌。老師替我倒了一杯,我淡淡地淺嚐了一口。
話題沒有間斷,我與老師相談甚歡,今天話題的主軸圍繞在宋明理學和文學批評上,羅清只是在一旁聽著,偶爾插口幾句。酒酣耳熱的快活僅僅是一瞬間,隨後而來的就是腦內血管的腫脹和不適感。我喝的不多,也足以讓人全身燥熱,頭暈目眩了。老師喝酒喝的挺急,不久後便開始胡言亂語,嘴上開始不安份起來,說起朱熹是個滿口仁義道德,行為噁心的可以的偽君子,最後竟直接躺在了地上,手像要抓取甚麼憑空之物一樣四處揮舞,全然看不出是個在課堂上神情嚴肅,不苟言笑之人。羅清扶老師進房,我收拾了東西,準備離開。
「洛水,多喝幾杯吧?」在我站起身後,羅清向我說道。
「師娘,時間晚了。」
「不晚啊,才9點多,快坐下。」
我答應了下來,實在難以拒絕女子的請求。剛開始,我們聊一些和老師有關的事。羅清指間擺弄的那根涼菸讓空氣蒙上了一層霧。後來,不知甚麼原因,話題突然忽悠轉到了李萍上。我和羅清說了些我與李萍近來的煩惱,她點著頭表示同意。酒不停地倒,就將要見底了,意識不清,眼前的景象就像是夢一樣。羅清雙頰泛紅,巧妙的擦去了臉上的黃斑,揭露經歷過歲月後特有的豔麗。
「你覺得很煩吧?對於結婚」。羅清紅著臉說道
「確實」,我不得不同意羅清的話。
「你是覺得李萍煩呢?還是婚姻?」
我被這問題問得說不出話,喝著酒思考該如何回應。跳動的血管搖動眼前的世界,萬事皆有定數,此時,圓桌下,羅清的腳不經意的碰到了我,酒精的眩暈使我沒有第一時間的向後縮。她的雙腿像是捕捉到了什麼,開始得寸進尺,先是趾間,慢慢的,足跟、腳腕、小腿,最後整條腿勾了上來,像條抓住獵物的蛇。
「他很久沒有了。」
圓桌上風平浪靜,桌下卻風起雲湧,我保持著托腮的姿勢凝視著羅清,羅清用已被酒精沾濕的朦朧雙眼回望著我。儘管眼神迷茫,我看穿了她眼中有股和方姍姍當晚一樣的渴求。理智又再次的對我告誡,「這是個考驗,不管什麼情況,必須記住道德,只因為道德十分重要,僅此而已。這女子已被酒精搞的神智不清了。所以,抽開你的腿,靜靜地離開這裡,不帶感情的道聲晚安,你只能這麼做。」我深吸了一口氣,準備抽開腿,羅清卻拉住我的手。
「他睡了」
短短三個字,就讓我拋開了道德的捲尺,現在回想,必定是那酒精惹的禍,是那酒精將原已不夠穩固的煞車給添上一抹油。我站起來,摟住她的腰,她放下根本不是用來盛裝威士忌的高腳杯,將菸拈熄,一把將我往飯廳後方的一扇泛黃的門裡拉。在昏暗的光線下,直到進到了門裏頭,才知道那後方通往著什麼。羅清沒有開燈,高的勾不著的通風口以死白的月光宣判著將要來臨的罪行。悶滯的空氣中瀰漫尿騷味,足以讓我辨別出那是廁間,失去敏銳的視覺卻沒有讓人失去本能。手游移在上臂、頷、頸、鎖骨、胸,繼續地向下摸索。此時的理智早已像失控的貨車,駛向通往深淵的斷崖。我們倆早已化成一股理不清的纏帳,勾結在一起。涓涓的滴水聲在狹小的黑暗迴盪,稠滯的空氣、興奮的汗水、被挑起的慾望,催促緊接而來的錯誤。我將她壓在潮濕的壁上,漸漸凋敝的山茶花在粗魯對待下重新盛開,我撩起她碎花裙的衣擺,像隻貪婪的蜂一樣向內搜索,將深青色的萼片從腿間扯下,撥開重重花蕊,取那久未醞釀的花蜜。再深、再深,一路地伸到了子房與胚珠,我嗚住了羅清的嘴,以免吵醒幾步之外的那隻老的不像話的蜂。他老了,沒了氣力再採蜜了,羅清對我耳語。花蜜因久未尋訪而肆意奔放,一直流瀉到了鬆垮的花瓣外,直流到了花梗,滴在了潮濕滑溜的地上。小室內,理性與道德沒了站立的空間,眼見多說無益,各自沈默的離開,僅留下淪喪敗壞的德行在耳邊喧囂叫罵,怒喊助陣。沒有目光的注視,山茶花邊緣的枯萎就不再重要,或許說山茶花已不再枯萎,因著這突如其來的走訪而再次的,回春了。
我在黑暗中整理自己的衣衫,不再碰一旁的女體。羞恥感讓我不敢面對門外的光線,羅清則是自顧自地理了衣衫,拉開門。回到飯廳,她像是全然沒事一樣輕鬆收拾著碗筷,又叼起了一根寶亨興致盎然地抽著,動作透露著自在,與我矛盾又綁手綁腳的身體語言形成反差。
「師娘...我先走了」
「是嗎?這麼快就要走了?不再多坐半小時?」
「晚了,剛剛...的事,沒發生過。」
「是嗎?」她對我投了個難以言喻的微笑,轉過身走向後門。
———————————————
https://www.instagram.com/vulgar_literature/?hl=en
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