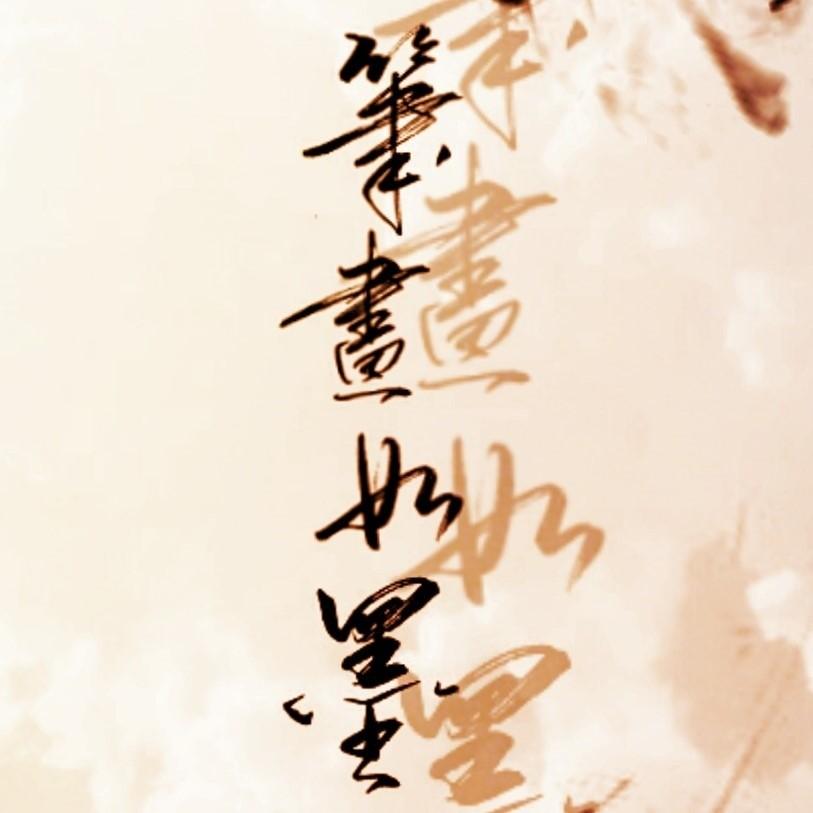白沫到底沒表面上冷靜,外頭的人看她沉著臉走出來,周圍散發出來的低氣壓把方圓五十公尺凍出一陣寒氣,連孟睿喊她都沒聽見,頂著一身陰沉,被眾人的目光送出工作室。
「跟云姊說我等會請假,有事直接打我手機。」
孟睿怕她那精神狀況出去要出什麼事,果斷告假跟了出去。
白沫腦子裡亂得很,各種雜音吊在腦袋上,像根繃緊的弦,因為那破事被撥動了一下,餘音縈繞,久久不散。聲音很雜,參差不齊、毫無規律,男女老少都有——笑聲、哭聲、哼聲,乃至幾個標點符號的沉默。
可能是真實的、可能是她臆想的,不管是哪個,一直侵擾她都是不爭的事實。白沫的臉上起了一層薄汗,臉色比平常蒼白了幾個檔次。心理瀕臨崩潰邊緣,哪怕表情還算鎮定,看上去都像苟延殘喘。僅需一觸,不堪的面具就會落下,露出醜陋的、還滲著血的傷口。
『嘻嘻嘻嘻……』
『噁心,原來是抄的。』
『就這麼想紅?名字連聽都沒聽過,三不五時就看到你。』
『這次又是誰啊?業務能力可以啊,抄出心得了?』
『哪個大神又被他看上,真夠倒楣的,好好寫個文也被這樣「借鑒」。』
『抵制!滾出文圈!』
謾罵、抹黑、誣陷——撻伐她的聲浪無處不在,知情的、不知情的,自以為「正義」的,好像看到「不公不義」的事就該出來發聲,彰顯一下自己的高尚情操。
文字就像刀,捅錯了、誤傷了人,毫無悔過地道歉之後把刀抽出來,傷口並不會跟著消失。哪怕過了,時間淡化了,也不會消失,留著一個猙獰的疤,時刻提醒自己,這裡被人捅過,曾經流過血受過傷。
可是又有誰在乎?
玫瑰凋謝了會有人替它下葬、偉人去世了會有人替他哀悼。都是被愛著、惦記著的事物。而又有誰會在意路邊凍殍的流浪貓狗,草地裡枯萎的野草,街邊猝死的無業遊民。都是不被愛著、隨時都能遺忘的東西——不對,或許從來沒被記住過。
白沫上了車,手下意識攥緊方向盤,油門一踩,藍寶堅尼駛著詭異的軌跡揚長而去。那輛車渾身上下看起來都非常「白沫」,明明是普通的車款,顏色也沒特別換過,但開車的人特別招搖,技術媲美賽車手。
為了防止別人家的三高在自己車上發作,很有自覺地忽視副駕駛座和後座,從不載人。
孟睿一路跟在後頭,他認識的白沫沒活到考上駕照的年紀,也沒特別去想,在這種情況下見到,完全沒做心理建設,被眼前的場景震得眼球生疼。孟睿自認遇過不少大場面,但眼前這樁真沒遇過。
白沫開車特別「瀟灑」,比男人還要男人,S行蛇行樣樣精通,把跑車開成賽車,堪堪踩著違規邊緣擦過。饒是孟睿都愣了幾秒才反應過來,他低罵一聲「操」,隨後上車跟在她後邊,生怕晚一刻就有人妻離子散。
白沫的油門越踩越兇,財大氣粗的如墨大神向來不在意罰單後面有幾個零,她現在精神狀況非常不穩,握著方向盤的手收緊,力道大得彷彿下一秒就能把那個圓環捏碎。
直到前面紅綠燈的綠光轉紅,她被迫停下,後知後覺發現掌心已經硌出一道紅痕。她隨意抹掉臉上的汗,深吸了幾口氣,才勉強壓下震耳欲聾的心跳聲。
「……還有完沒完了。」
她伸手一摸,車裡的空調溫度低,但後背沒有半塊布料倖免,濕了一片。折騰了好一會兒,時間不過正午,豔陽高照,街道上人來人往,被某人高超車技「震懾」的路人不在少數,大多嚇得暫時性失語,彷彿目睹了一場玩命關頭。
至於半路上被她驚天地泣鬼神的車技耽擱到的司機不斷罵娘,讓她不會開就別出來禍害別人,就怕一個不小心害別人家破人亡,仇恨拉了滿路。但這人功高不愧是高,直接選擇性失聰,全當沒聽見。動靜這麼大,沒搞出什麼命案現場,也是個神人。
白沫一個甩尾,愛車恰巧甩進了一個停車格,在途中劃了一道完美的弧線,「嘰──」了很大一聲,好似能把那些擾人的聲音全都甩出腦外。孟睿在她不遠處停車,覺得自己追著一路血壓飆升,跟不久前一覺醒來看見某人突然詐屍時的驚悚感比來有過而無不及。
他抹掉被某人嚇出來的冷汗,踏出車後的步伐穩健,全然看不出片刻前的狼狽。他徒步走到白沫面前,無視了對方詫異的目光,開場白愚蠢至極:「真巧,如墨大神。」
他悠哉看了手邊的錶,理所當然得好像他們本來就有約,錶上的指針動了一下,正好指在一上,他又說:「遇見也是緣分,吃個飯嗎。」
孟睿的心理素質自來到這裡後直線上升,睜眼說瞎話不帶喘氣的。
「好啊。」眼前這位更不用說,笑得沒心沒肺,方才胃裡翻騰的黏膩感宛如一場幻覺,消逝得無聲無息。
正午的太陽很烈,行走在陽光底下的人們無一不加速前進,生怕再拖個一秒就被烤成人乾。
孟睿身上的襯衫已經濕了一片,熱的。他走在前頭,選了面前一間有冷氣的簡餐店走了進去。白沫殿後,她面色無常,一雙手揹在後頭,一隻手悄悄地攥住另一隻手的指節,把身體上任何可能引發孟睿皺眉的因素一概壓下。
白沫開車開得猛,一路上孟睿顧著跟車還有注意這傢伙有沒有鬧出人命,其他的無暇顧及。現在精神稍稍鬆懈之後才發現白沫停車的地方是他家附近的小區,簡餐店也是之前跟陳筌佑會談時的那間。
這都是些什麼事?
一個人若精神狀況極不穩定,要嘛開回家、要嘛跑去喝酒,哪怕不是深夜,萬里無雲、太陽毒辣,選擇也不該如此奇葩,在路上上演了蛇行跟180度甩尾,結果卻在一間簡餐店前偃旗息鼓。太玄幻了,他真真摸不清這些作家的腦迴路。
「妳就這樣翹班出來沒關係?」
「沒關係啊,基本上我在那也沒什麼事,看著席寧仁我也是煩,寫不出任何東西。喔,我要義大利麵,奶油的。」
白沫吸了一口奶茶,要不是孟睿跟了她一路,看見她怎麼飆車跟危害行人安全,幾乎要被她精湛的演技騙過去。孟睿叫來服務生點餐,把帳結一結後又把目光移到她身上。
「妳跑來這幹嘛?」
「來餐廳除了吃飯還能幹嘛?」白沫不明所以。
孟睿撐著一隻手看她,「妳那精神狀況還能吃飯?真不怕在路上把誰給撞死嗎?」
「喔,這個你放心,我對載人雖然沒什麼信心,但在不要鬧出人命這方面我還是有研究的,妥的。」
「……」妥個毛線。
白沫勾著笑容,眼尾彎彎,「開玩笑的,當然是想跟我們筆畫大神吃一頓飯才來這裡啊。」
孟睿直接忽略對方揶揄的眼神,「你們以前也會在這吃飯?」
白沫頓了一下,表情倒是沒變,「還好,隨便哪都可以,不一定要這裡。」
說話的空檔,她點的義大利麵已經來了。孟睿剛看了街頭賽車場面,覺得胃還在攪,只點了一杯綠茶。
白沫吸了一口麵,道:「反正你也知道了,我還是要來跟你談談封面的事。」
她看了孟睿一陣,確定對方的神情無異之後才接著說,「《失而復得》的封面你可能也猜到了,這篇文是在一個月前開始寫的,也就是在你剛來的那陣子。」
孟睿沒說話。
「我是以你為原形寫的故事,沒有你這個故事就不會存在,封面也只能是你來畫。」
「妳真沒事?」
「我沒事啊,你也看到了,就算剛剛有點問題,現在也全好了。」
「手。」
白沫伸了一隻手出來,卻見他搖頭:「不是這一隻,是左手。」
白沫的呼吸滯了一瞬。
「妳以為我不知道?」
孟睿直接把她藏在後面的手拉了出來,看到指節上的紅痕,一雙眼睛平淡無波,「妳以為只有妳了解青梅竹馬?妳應該還有什麼事沒告訴我吧?」
她沒說話,麵也不吃了,臉上的笑容歛了下來,進行無聲的抗議。
孟睿嘆了一口氣,「這事我很有經驗。」
說起來也不是什麼值得一提的事,現在想來覺得也挺荒謬。抄襲這事就是百害無一利的東西,不管是抄還是被抄,只要被扣上這頂帽子,都會受到波及,一舉暴露到槍口上。
他用如墨這個身分發表文章時或多或少會被波及,可能是抄,可能是被抄,因為他那時還不紅,總會被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定罪。到最後那些「正義使者」只會假惺惺地說:「抱歉,我不知道你也是受害者。」
除了被傷害的人,又有誰會在意呢?也只是把那些傷藏著掖著,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
白沫靜靜看他,沒發表任何高見,或許在這個圈子是常態,好像沒經歷過就不是作家,但它無疑是最令人難受的。你辛苦了很久的東西被人用兩個字抹滅價值,成為那些人口中「不值一提」的東西。
他們周圍似乎形成了一個無形的圈,將四周所有喧鬧隔離,獨留落針可聞的空間,靜得快讓人窒息。
「我會畫好封面,有什麼要求儘管提。」他選了這句話收尾,有些事不需要說得太詳細,只是讓雙方難受罷了。
白沫依舊沉默,只是這次抬起了頭,朝他一笑。